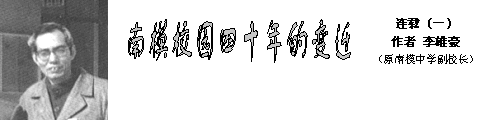
走进南模
1963年8月20日上午,铅色的天空,蒙蒙细雨,我们大概有20个左右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,陆陆续续地跨进天平路200号南洋模范中学的大门。就从这不怎么显眼的校门说起。它的位置在现校门往北30米左右,即现在的小红楼(同一楼)旁边。
小门旁边的一间房(小红楼的底层),门窗面南而开,便是传达室,房后有一座木楼梯通向2楼。2楼是极简易的两间,一大一小,都是用铁皮、油毛毡铺顶,作为教师宿舍,后来,我们几个语文教师被安排在这间小楼里住宿,夏天太阳直射,室内像蒸笼一样闷热。
我们这十几个年轻人都是前来报到的新教师,各个学科都有,光我们语文教师就有5位。大家先一起集中在红楼底层的第一实验室。当时接待我们、并领着我们在不大的校园里兜了一圈的是原教导副主任韩先生。为了叙述的方便,就从进大门以后说起。大门是面向东的,进门后,左边(即南边)靠天平路围墙是几间简陋的木结构平房,这便是教师食堂。往前走,由东向西,便是一排六间教室,称之为“南平房”。南平房沿着不太高的围墙修筑,围墙外面便是另一所学校(华光中学)的操场了。进门后的右边(即北边),离传达室不远,靠着围墙也有一排六间教室,与“南平房”遥遥相对,称之为“北平房”。它的北边围墙外面,是一片大花园。靠着“北平房”南面有一座装上门窗的亭子,称之为“八角亭”。亭两边各栽有一棵紫藤树,盘根错节,枝叶繁茂,到开花的季节,缀满了淡紫色的花朵,据说它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,是一道引人遐思的风景。“八角亭”和“南平房”之间,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,从校门口一直通向深处。
沿着小路往里走,便见一幢3层的楼房,外墙用红砖砌成清水墙,故称之为“红楼”。红楼的2楼朝南伸出一个大阳台,阳台上搭了一间东西两面开窗的小屋,阳台的底座下挂一只大钟,这便算是钟楼。学校的工友按时来敲钟,便是上下课的信号了。这幢楼在当时是南洋模范的教学主楼。对它的内部结构下文再作详细介绍。在红楼和八角亭之间有3间木板房,这是用作教师上课前的预备室,里面放着“教室日志”、粉笔等上课用品。钟声一响,教师们从里面夹着“教室日志”出来走进课堂。预备室的大桌子上也放着几张报纸,兼作教师的休息室。用现在的眼光来看,这几间平房像是危房简屋,但几位老教师课余在里面翻翻报纸,聊聊天或者批几本学生作业,倒也怡然自得。
红楼的西边是一片不大的操场。操场的北面是图书馆,一幢红瓦盖顶、灰色外墙的2层楼小洋房。1949年以前,在男女生分校学习的时代,这里曾用作“女子部”,外面用竹篱笆与男生隔开。操场的西边靠华山路围墙有一排3间平房,作教室用,称之为“西平房”。在西平房的南面,有一幢3层的楼房,称之为“西楼”,每层两间教室外面有走廊,教室南北通风,可算是南模校园里条件最好的教室了。
西楼的西北边靠华山路,南边是一块空地,学生课余喜欢在这里踢小橡皮球。空地的南边有一间木结构的礼堂,里面有木头柱子,摆满了两米多长的木条凳,大概可容纳五六百人集会。礼堂旁开一扇边门,可直接通华山路。礼堂的东南方向,又有一幢小洋楼,比图书馆那幢更小,不能做教室,用作工会活动室和教工宿舍,而底层作为体育教师办公室和体育保管室,学生课余常来这里借篮球。这幢小楼南面靠康平路,东面与华光中学接壤,至此,便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南洋模范中学的边界了。
回想起来,20世纪60年代初“文革”前的南模,有几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:一是“清贫”。人们常说学校是“清水衙门”,从南模那两扇破旧的木门看,只能说是“清水破庙”。二是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,小而有序。总共十多亩土地安排得有条有理,大体上是:初一年级安排在南平房,初二年级安排在北平房,初三年级安排在红楼,高一年级安排在南平房的西头,高二年级安排在西平房和西楼底层,高三年级享有最优惠待遇,安排在西楼的二、三层楼。当时我担任高三(2)班班主任和(2)、(4)班的语文课,就一直在西楼2楼和3楼上课。秋冬的晴日,走廊上洒满和煦的阳光,课间我常常和学生靠在教室外走廊的栏杆上,聊天晒太阳。三是快乐,我们这十几个年轻人,来自四面八方,但都是乐观主义者。后来听校方说,这些人都是校长亲自去上海师范学院从毕业生中挑选来的优秀生,因为南模的老教师在50年代被抽调一空,元气大损。在我们这些年轻人中间,有几个人的家在郊县或江苏,我们几个上海人也“轧闹猛”,对校方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住校。这使学校领导措手不及,只得将大家分别安排在几幢小楼里。尽管6个人挤在一小间里,睡双层叠铺,一个月48.5元工资,但教师生涯刚刚开始,白天和学生在一起,晚上坐在小楼里备课、改学生作文,或者几个人嬉笑着谈论工作中碰到的问题,小楼的灯光,总要亮到午夜。有时五六个人结伴到虹桥路华山路口的小店去吃夜宵,大饼油条豆腐浆,美味可口,真可谓“辛辛而不觉苦苦”,生活充满快乐。清贫而快乐,是当年生活的写照。